-
連結
A:「我說,你坐在窗台上是為了什麼?」 B:「偶爾我會想像往下墜的風速、落地時的碰撞聲,並且猜測當下我的人生跑馬燈會出現什麼畫面、猜測我當下會不會後悔、想像電視新聞會如何報導、幾天後會被忘記。」 A:「聽起來,你沒有什麼非死不可的理由對嗎?」 B:「沒錯,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苦痛。既沒有經濟上的重擔,也沒有失戀,更沒有什麼夢想破碎的衝擊。」 A:「但總是有些理由,促使你去做這個行為吧。」 B:「確實,我突然想到了。我還會去想像有人會為了我哭泣的模樣,究竟會是誰呢。其實多少還是會好奇這件事。」 A:「原來如此。」 語畢,B縱身一躍。 雙腳踏回房間的地板。 B:「如果不是你跟我說話,通常我的雙腳都是放在屋外的。」 A:「因為你認為我是其中一個會為了你哭泣的人嗎?」 B:「也許吧。」
-
講不清楚
那就用寫下來好了。 感受太多、想說的太多,三兩下就會失焦。想要寫下來卻又不知道應該怎麼寫,也或許其實問題出在期待過高吧。 期待自己能夠有條不紊說出想說的、能夠輕輕鬆鬆打出一個內容結構嚴謹、言簡意賅的文章,卻發現原來用寫的也跟用說的同樣困難。實在是沒有辦法很清楚描述自己的想法,只是不斷給自己壓力和期許。 也許是因為習慣了解釋,但其實或許沒必要說那麼多,畢竟都是說給自己聽的。既然是說給自己聽的,那有沒有結構可能也不是那麼重要了吧。前提是自己先放下期待,然而「自我期許」究竟該如何權衡,這又是另一個議題了。
-
都知道但做不到
也或許有可能,只是做不到100%,但可以做到50%。 下意識的感受來得太快,常常是在意識控制大腦以前就不知不覺壟罩整個頭頂,不安、擔憂、自責…或任何感受到不適甚至影響表現的思緒。 明知道自己並不是正在被責罵、或是現場環境其實並沒有造成危險,卻因為過去受到的傷害產生一連串的反射動作而下意識開始防備、警報響起想法亂竄。接著才有可能突然想到事實和想法是不同的兩件事,現狀在客觀上沒有那麼糟糕。 然而,當自己越是能意識到「我又掉進去了」,反而越容易感到氣餒。那是一種感到很絕望的感覺,是一種「怎麼又來了」的感覺。 如果可以,多希望可以完全阻擋下意識而來的恐怖思緒,但卻是一直重蹈覆轍。即使知道自己事實上有進步,卻總是因為狀況再度發生而感到不悅。追求著100%卻無視從30%進步到40%,從40%進步到50%的事實。 也或許,必須接受可能有「無法完全根除」的可能,才能夠放自己一馬吧。
-
能得到新想法,就不是內耗
「想太多」是一個常被拿來貼的標籤,而這陣子隨著心理學知識越來越普及之後被換成了一個聽起來更有深度的名稱:「內耗」。 每當因為想法比較纖細、顧慮較多時,旁人常會希望你「不要想太多」,不然就是直接搬出「內耗」兩字來對你說教。而你可能也會因此掉入一種自責的陷阱。 是阿,我只是一直在內耗而已。 人人都是心理醫生,急著幫對方開立名為「內耗」的診斷。而這個診斷有什麼用處嗎?並沒有。只不過是把自己可能顧慮的事情多加一項叫做:「我又在內耗了。」 有時候確實是在「內耗」,但也有時候不是,判別的方式就如本文標題:「能得到新想法,就不是內耗」。可以試著去感受自己的念頭,並且: 人生搞不好根本沒有正確答案。執著於某種答案或許會讓自己內耗,但並不是追求答案的過程都叫做內耗。我認為追求答案的健康方式,是當作自己在探險,不求一定要一次找到終極解答,而是在探險的路上讓腦袋裡的畫面越來越清晰。直到有一天自己會拼湊一個答案,使自己感覺到「啊,可以了」 這讓我突然想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句話。
-
不愛自己怎麼辦
不怎麼辦。不愛自己就不愛,想恨就誠實去恨。 也不用把愛當作是萬事萬物的一切解方,搞不好這世界的愛其實是有限的資源,有些人註定貧乏、甚至可能無法得到他所需要的最低需求門檻。 人們總強調愛,導致我們都被蒙蔽了,誤以為沒有得到愛就會招致滅亡。因而汲汲營營、患得患失地煩惱,才發現或許該從自己身上討愛。 但問題是,這個發現也是別人告訴我們的,時常是知易行難。卻又因為已經認為別無他法而感到惶恐,排斥這個無法愛上自己的自己。 不用強迫自己去愛任何人,更不需要強迫自己要愛上自己,這種非愛不可的執念其實才是痛苦的根源。悲傷不是來自不被愛,也不是沒有對象可以愛,而是強迫自己去愛上一個自己不愛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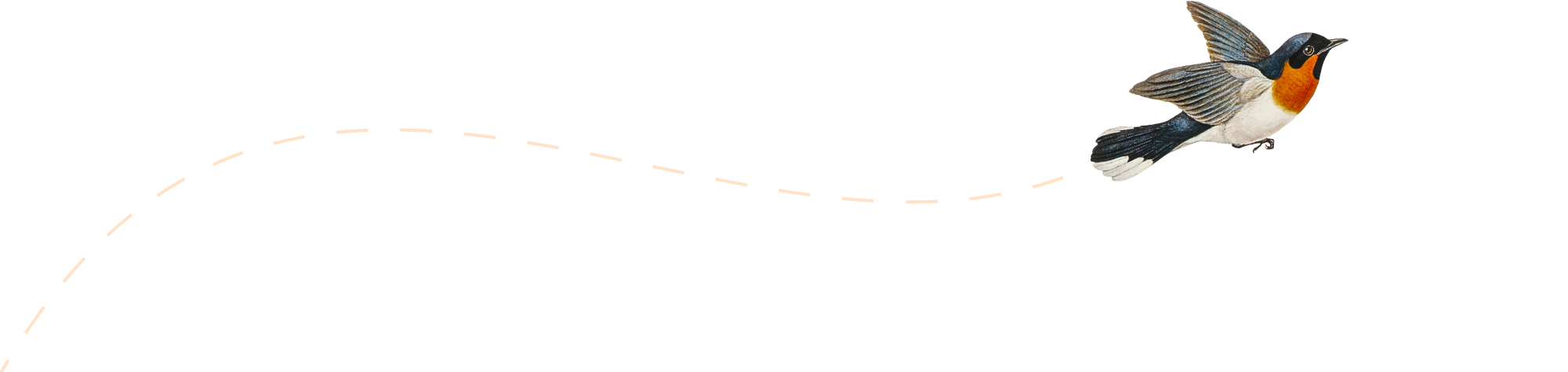
既然心情不好躲不掉,那至少要搶回詮釋故事的主導權